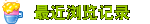1990年8月12日,我和丈夫在北京后勤部招待所对外营业的歌舞厅,举行了盛大而又节俭的婚礼,婚后第一年的纪念日,我们这两个象是“小孩儿过家家”的大男孩儿和大女孩儿再次穿上了结婚自制简易礼服(注:当年为了节约开销,我没有要求租婚纱,他也没有买礼服)来到了市区的一家歌舞厅。记得那天我不顾丈夫的反对(他很矜持和节俭)花了10元钱请乐队歌手专门为我俩演唱了一首邓丽君的歌曲,我们夫妻轻拥而舞……
婚后第二年的纪念日,我抱着不到两个月的儿子(注:这个与我们太有缘的孩子属于“不期而至”!),丈夫抱着那把心爱的吉他,一起深情地唱起了结婚典礼时他选定的对唱歌曲《如果》:“如果你是朝露,我愿是那小草,如果你是那片云,我愿是那小雨……”
婚后第三年的暑假,丈夫自费去省城进修本科,纪念日前夕,他寄来了一封信:“八月十二日这天就不能和你共同度过了!我给你留下了礼物,在影集边上的小包里,作为我一点心意,本来想给你留下几首自弹自唱的歌曲,名字都想好了,儿子哭闹的缘故,没能录成,90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我觉得和你在一起生活很幸运,善解人意的你减去了我不少烦恼……”礼物是什么我记不清了,可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。
接下来的纪念日每年照旧,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依稀觉得好象在走形式,那份曾有的喜悦已逐渐被淡漠代替,我们象很多夫妻一样,进入了感情的降温期。我和他在性格上的差异日见清晰:他,固执倔强……我任性随意…….,我们开始为一些小事争论不止(注:毕竟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环境,观念差距很大!),虽从不大吵大闹,但从此心里有了距离。这种冷淡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多年,期间我曾提出过分手的打算(注:当时协议都已写好只是他不肯签字)但都因孩子的意外出险而搁浅了(注:过后我总是在想:也许孩子是上苍派来维系我们感情的“使节”)......终于我意识到这样下去结果只能是各奔东西。为了可爱而无辜的孩子,为了年迈守旧的双亲,也为了我们难以忘怀的过去(注:他在我眼睛被医生宣布可能会失明时,毅然决然放弃毕业前的紧张复习陪我去医院接受治疗),我们终于坐下来真诚地向对方检讨了自己,然后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愿。他建议我:“在注重形式的前提下再增加一些具体、实质性的行动(比如:我不会做家务)……”;我告诉他“光有行动缺少应有的表白也不行!(他的言语很少且有些生硬的表达方式让人有时难以接受)……”,我们握手言和,温暖的阳光重新照到了这块小天地。
去年的纪念日,我满怀感慨地写了一篇文章《牵手》并在当地电视台为我们的结婚十周年点播了同名歌曲,以庆贺我们刚刚结业的人生必修课:婚姻磨合期。记得文章的结尾的一段是这样写的:“他确实不是一理想中的爱人,但他却是一个值得终身依托的好丈夫,我愿继续与我的丈夫携手同行,共创和谐的婚姻。”